在全球性的私人股權基金投資熱潮中,經濟高速增長的中國是全球覬覦的狩獵場,但在政策尚未完全放開的中國,PE面臨的可能只是表面繁榮
無錫尚德太陽能公司在紐約的上市不僅造就了一個中國首富,更讓一批背后俗稱“PE”的股權投資者獲得了十幾倍的高額回報。
“尚德是我在國內的第一個項目,非常成功。”法國NBP亞洲投資基金合伙人王剛是第一個發現尚德這個潛在項目的PE投資人。作為首席投資商,王剛協調高盛、英聯、龍科等其他幾家聯席投資者,幫助尚德書寫了在美國資本市場的神話。
幾乎每天,都會發生PE對其他企業的重大收購。PE是Private equity Fund的縮寫,俗稱私人股權投資基金。它和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對沖基金為典型代表)不同的是,PE主要是指定向募集、投資于未公開上市公司股權的投資基金,也有少部分PE投資于上市公司股權。
NBP亞洲投資基金對尚德的投資取得成功以后,又陸續在中國尋找并投資了六個項目。其中四個現在已經退出,獲利豐厚——NBP在中國大陸地區的總投資額可能只有區區幾千萬美元,但四家公司的投資回報率則超過100%,利潤達到2億美元左右。
NBP基金的投資軌跡正好描述了PE運作的規律:以戰略投資者的身份進入公司管理,在獲利之后逐漸退出。
無論從資本市場的制度完善還是開放程度來說,在中國或印度這樣的新興市場進行大型股權交易并非易事,但這里為國際投資者提供的大量機會令他們著迷。一位國際PE基金經理說,他能真切感受到有成千上萬的公司需要發展資金。
英國宏信環球投資管理公司(Henderson Global Inverstors)是一家管理著1300億美金的全球性資產管理公司,在倫敦和澳洲主板上市。宏信北亞區投資總監舒明博士表示,中國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戰略重點,尤其是在直接投資方面,“宏信中國”相當活躍。
PE在亞洲地區的“資本狩獵”從五六年前就開始了,直到2006年一系列明星企業的聲名鵲起,才使得幕后推手PE進入大眾的視野。PE熱首要的原因是中國、印度等亞洲經濟大國的爆炸式增長,例如在2006年,私人股權投資領域就募集了320多億美元的亞洲投資資金。進入2007年,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橡樹資本(Oaktree Capital Management)以及Cerberus資本管理公司均宣布了亞洲業務擴張計劃。
法國NBP旗下管理25億歐元基金,其中用于亞洲地區的1億歐元中最初只有30%用于投資中國大陸地區。但隨著一個接一個項目豐厚的回報,這個比例增長到了80%。
不可否認,PE的興盛是今年全球特別是亞洲金融市場的一個重要現象。摩根士丹利前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PE的繁榮有實際的數據作支撐:2007年上半年,PE籌集了2400億美元資金,預計今年將超過去年的4590億美元。而1991年,整個行業的籌資總額僅為100億美元。
低調的巨額回報
PE對一家企業的股權持有期一般是3-5年,這決定了PE不可能走像投資銀行IPO那樣對企業“游說、完成交易、拿了雇傭費走人”的路徑。
宏信的舒明說,當決定投資到一家中國或印度的企業之后,宏信都會參與到企業的管理中去。正因為PE和企業在利益上長期捆綁在一起,因此當它通過投資和股權交易成為公司重要的股東以后,就可以通過改造董事會、改造管理層,為企業未來的發展在戰略上重新定位。
“現在很多公司的董事會一團和氣,是紳士俱樂部,改變‘你好我好大家好’現狀是非常難的。”美國弗勞爾斯投資公司(J.C Flowers)董事總經理宣昌能說。他認為PE進來之后才能實現“用手投票”,激勵機制使得PE能夠非常關注企業的成長與創造價值的空間,真正可以起到完善被投資對象治理結構的作用。
弗勞爾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專注于金融服務業投資的收購基金,由華爾街傳奇人物之一、高盛前合伙人弗勞爾斯創辦。他們在亞洲最得意的項目就是收購日本長期信貸銀行,并取得了成功。現在,弗勞爾斯把目標鎖定了中國。
PE種類繁多,目前在國內比較活躍的、規模較大的PE比較偏好投資的主要是“初創類企業”的風險投資基金,“擴張型企業”的增長型投資基金以及投資于“并購市場”的并購基金。同時,PE在提供過橋資本、投資于上市公司股權和行業投資(如房地產私募基金)方面也非常活躍。
國際PE在中國已經有很多成功的例子,最重要的是,他們的收益以驚人的速度增加。高盛直接投資部一位人士說,從創造利益來講,最近幾年高盛投資部門創造了幾乎更多的利益,“如果我們做工商銀行的IPO,傭金最多四五億美金,但是我們進行了直接投資,到目前為止賬面上已經賺了六七十億美金的利潤。”
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2002年底,摩根士丹利、香港鼎暉、英國英聯三家公司一次性向蒙牛投資2600多萬美元,共持有蒙牛乳業約32%的股份。2003年第四季度,這三家國際投資機構再次向蒙牛增資擴股3500萬美元。隨著2004年6月10日蒙牛在香港成功上市,蒙牛一躍成為國內乳業巨頭,總市值接近300億元,三家投資人也賺得盤滿缽滿。
中國銀行相繼在香港主板和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之前,引入了4家私募股權投資機構:蘇格蘭皇家銀行、亞洲金融私人有限公司、瑞士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分別投入30.48億美元、15.24億美元、4.92億美元和7374萬美元。中行上市后,按A股發行價計算,這4家投資機構大約獲得2.6倍的投資回報。
一位長期觀察PE發展的財經界人士這樣形容:“它們(PE)在中國獲得了巨額的回報,可是一個個都那么地低調,仿佛世家貴族。”
事實上,PE恰恰是歷史很短的一個行業,世界上恐怕還沒有超過40年歷史的私人股權公司。1970年代全世界的PE加起來可能不超過百億美金,現在據不完全統計,估計規模已經超過1.5萬億美金。
對于PE行業發達的美國來說,PE的發展就是以市場來檢驗,誰有本事把錢管好,市場就把錢投給誰。著名基金KKR最初就是三個人做起來,30年后,KKR完成了超過150起交易,涉及企業的總金額超過2790億美元。
集全球資源
PE在資本市場的霸氣日漸顯現,引起了很多研究機構的興趣。上海證券交易所一位人士認為,企業在初創階段,風險大而銀行不愿貸款,因此“風險與收益共擔”的PE對初創企業的發展意義深遠。
企業獲得戰略投資人的資金后,可以迅速擴大生產規模,提高公司的贏利能力,使公司在公開上市時獲得更好的估值。而企業在上市前期,一家知名的海外戰略投資人或風險投資基金,不僅能夠提升公司整體形象,在資本市場上對公眾投資人還具有明顯的號召力,提高上市時股票發行價格和融資效果。
PE在全球的名聲和資源可能對企業的上市和擴張起著關鍵的作用。目前上海一家綜合媒體公司正在圖謀打包上市,該公司高層正在積極尋求合適的投資者進入,而他們考評的第一個指標就是:是全球有名的投資人么?——投資人的名聲和資源直接影響這家公司上市后的融資額。
一家全球的股權投資公司,確實可以憑借積累的資源來進行全球范圍的調配。舒明就非常自信,自己服務的英國宏信基金能“集全球的資源”為某一個具體國家的投資來提供幫助。在亞洲,不同國家的產業發展速度是不一樣的,宏信在印度的醫療醫藥、技術服務兩個行業做了很大的投資,并參與了企業的管理。這兩個行業在印度發展要比中國快,因此宏信在其中得到的產業經驗和管理經驗,對以后在中國投資同類型的企業有巨大的幫助,可是使之投資的中國企業走得更快。
私人股權投資基金支持了高成長企業的發展,為資本市場源源不斷地提供了上市資源。因為PE往往要面對多個投資者,每個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各有差異,需要一輪一輪地談判,他們所做的就是要為大家找到一個利益平衡點。
很多人認為PE從投資的企業獲利主要是通過企業上市。舒明認為,上市只是臨門一腳,而PE在三到五年的持有期內可以幫助一個企業做很多事情,使企業本質上變好,那才是PE創造價值的地方。
英國TRIALPHA資產管理公司資深項目分析師陳嘉子表示,PE退出的方式有很多,如通過企業上市向資本市場賣出私人股份,或者把股權轉讓給企業管理層或其他投資人。“當然現在股市非常好的情況下,IPO當然最佳,立刻可以翻很多倍。”陳嘉子說。
充裕的資金為中國私募股權市場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資本基礎。清科研究中心統計,去年一共有40只可投資于中國大陸地區的亞洲PE成功募集,募集資金高達141.96億美元,下半年募集金額則一下子比上半年增長106.5%,共有中外75家PE參與對129家大陸及大陸相關企業進行了投資。
高盛亞洲并購業務負責人雷俊(Johan Leven)說,中國的經濟發展為包括金融服務業在內的海外投資者打開了新的領地,中國客戶需要世界級的咨詢服務,需要帶給他們最好的機遇和視角。
風光后的風險
很多外資PE已經在中國國內設立辦公室,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家外資PE獲得批準正式在國內設立公司。而直接以人民幣作為基礎貨幣投資,政策上更是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
“現在國內關于PE的討論也非常熱烈,就是如何從政策上真正以人民幣為基準貨幣來投資。”舒明說。現在大多數PE投資采取的方式是在海外某避稅港注冊,然后投資到國內,以美元作為基準貨幣。
對PE來說,投資的考量是首先判斷一個國家是不是有投資環境、有沒有好公司。第二個要考慮的是政策環境,導致投資者決定該用怎樣一個模式去做投資。舒明認為,國內的投資環境顯然是越來越好的,同時能發現很多好公司。
王剛認為現在國際PE扎堆中國是因為投資這里的企業回報比較高,而在美國和歐洲投資的一些企業相對來說成長性和回報率都偏低。況且國內有很多優質的、處于幼稚階段的公司,它們伴隨著宏觀經濟一起成長,成長性一年能達到50%甚至翻番。
目前可能的一個政策風險是,證監會希望更多的優質企業能夠在國內上市,因此,一些企業的海外上市計劃遲遲不批。這導致業內對海外PE的離岸投資今后是不是還能長期運作持懷疑和觀望的態度。
“現在國內的企業海外上市的大環境肯定是不如2007年以前好了,主要就是政策風險,證監會一家就可以靠政策卡很多事情。”一位PE投資人說。
這位人士表示,解鈴還須系鈴人,政策造成的問題必須靠政策來解決。政府造成了這個結果,必須給一個新的政策去解決,要么把原來堵住的路重新打開,讓紅籌路重新走通。要么另開一條路,讓人們可以把錢投進來。
無論怎么樣,目前國外資金進來中國還是有限制的。中國政府不喜歡短期的資本投資,除非金融業的一些戰略投資人。
美林亞太區并購業務主管戴凱寧對這方面也深有體會,他認為除了要具備產業和產品專業知識外,懂得如何應對監管環境以確保交易順利進行相當重要。
對于國際PE的一些政策,高層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表態。7月8日,中國證監會研究中心主任祁斌在“第一財經研究院”成立論壇上表示,產業基金和私募股權投資基金是推動資本市場的可持續發展的力量。“我們認識到,要實現中國資本市場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建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和產業基金跟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關系。”
在貨幣政策層面,PE也面臨另外一個風險。近來貨幣利率升高,美國在升、英國在升、歐洲各國也在提高。當各國的央行都在升利率的時候,投資就變得越來越難了。過去兩個星期,已經有幾家國際大PE在歐洲拆借資金都出現問題。
“借錢的成本變高,對PE的投資就造成問題。現在利率拼了命地升,而投資的回報又不是那么快。”陳嘉子說。
加息對于股權投資是負面的因素。股權和債券作為互補的投資方式,加息導致投資在固定回報上的成本更高,因此股權比以前的吸引力會減低。不過舒明認為,加息帶來的負面影響還不是很明顯,因為國內利息實在太低,加了半天如果還是很低的話,那么這個效果就不是很明顯。
簡單來說,利息更多的時候,借錢就變得比較貴,總的回報就少了。這是一個一環扣一環的邏輯:PE經理最大的問題就是利率漲的時候借錢比較困難,新的投資項目就沒錢投,以后幾年就沒有投資回報。
PE做出一個投資之前,最重要的工作是盡職調查,評估企業投資的價值。謝國忠否認了目前PE熱衷的科技行業的技術內涵,他認為中國很少有真正的高科技企業,企業更多的是靠商業模式而不是技術,他甚至奚落做太陽能電池板比制鞋還要簡單,因此從長期看,這些企業的盈利率不會表現出色。
謝國忠還認為PE所需的大多數核心技術在中國并不具備。因為中國幾乎不存在杠桿收購市場,沒有一個復雜的債券市場來為這樣的交易融資。因此PE 的繁榮在中國、至少在目前的中國,只是一個虛幻的泡沫。
即便如此,在中國的PE基金經理們還是忙著整天找項目。工作還是要繼續,任何希望長期在中國工作的投資機構都必須如此。“如果現在有一點困難就撤出全部團隊,今后再進中國就落后于別人了。”一位PE經理說。
安徽新華電腦學校專業職業規劃師為你提供更多幫助【在線咨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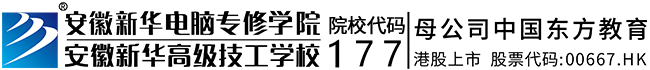

 熱門精品專業
熱門精品專業

